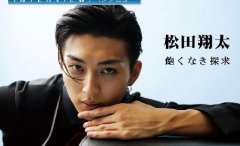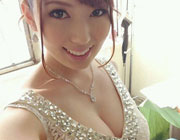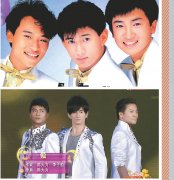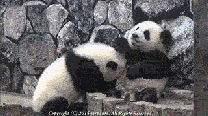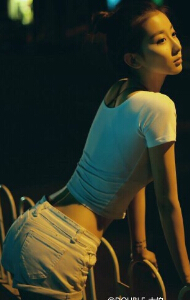段奕宏:戏里戏外完全不是一个人(3)
萨郎
说到喝酒吃饭,有一顿饭让好几个人难以忘却。
拍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时,剧组经常去吃酸汤鸡火锅,一开就是好几桌。有天,刚下完雨,菜全上来了,大家坐着聊天。
“大圆桌旁边有棵大粗树,刚下完雨,我特开心,啪,一脚踹那个树,树上的水‘哗’下来一桌子!”段奕宏回忆。
“我X,国强你他妈干嘛?”兰晓龙当场就骂。“国强不在,我当时傻了,我说我踹的……哦,老段踹的,那我可以原谅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老段很少做这种出格的事,他应该多做这种事。”兰晓龙回答。
回想起来,段奕宏自觉好笑,很快又正色:“嗯,我就是没法很轻松地面对每一个人。哪怕我们都一起演了两部戏。”戏由人生,老段也明白自己的问题:“从大学起,我就是一门心思关心自己这点事,不闻窗外事,给别人感觉心事重重的,不懂得张弛。”
铁哥们儿高虎和段奕宏友情长达20年,在寝室里的床铺头碰头,到今天他都叫段奕宏“龙龙”。说起“龙龙”的“自闭”,高虎直说“可恶”。
刚入校,男生们常会去学校附近的南锣鼓巷、王府井逛逛,看看女生,闲聊、抽烟。段龙同学每天不是排练厅,就是图书馆,宿舍。即便大一就已经被同学争着搭戏,依然充满危机感。
“我是个完全的乐天派,没心没肺一个东西。他三棍子闷不出一屁,一拳出去没反应。可气的是吧,他明明有渴望(要加入我们),就是克制住了。”
陶虹是北京人,那时段龙很少回老家,周末她经常会邀请他到自己家来吃饭。“他总是不好意思,说我回头请你来宿舍,用电磁炉给你做手抓饭吃吧。我们都觉得他的礼貌有点多余。”
他怕亏欠,怕负担不起同学、朋友的关怀,所以好多年里,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。但在距离边境咫尺的新疆伊宁长大,段奕宏身上又天然有股“什么都不怕”的劲头。母亲叫他“萨郎”--新疆话里“一根筋,脑袋容易充血”的意思。
因为在家年纪最小,“被收拾得最多”,逆反心理就更强。家里人说当演员是不可能的事,“谁让你从小给我订《上影画报》、《大众电影》的?”
从小做着电影梦,中间有很多次把自己给“拍死”了,还是没死心。考大学,连着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中戏,前两次没考上,回程火车上一遍一遍地想词儿骗家人,想着想着自己也信了。那股拧劲儿毕业后也没消散,段奕宏将之定义为“无知的盲目”。
张建栋记得,在《刑警本色》组里,总有些年轻演员围拢老演员,“捧着”敬着,陪吃陪喝。有一天,段奕宏忽然冷冷地问导演,“我能不陪着吗?”
“太能了!”张建栋叫好。“剧组也是江湖,总有人不高兴。段龙好像无所谓,‘得罪就得罪吧。’我也这么觉得,只要戏上面好,何必管别的。”他在这个“刺头”身上看到了自己。“刚毕业出来的学生,多半都是乖巧服从的。敢坚持自己的不多。段龙有我特想做的那种姿态。在他身上,替我过瘾了。”
已经成为“老段”的段奕宏说,年少时的自闭是一种自我保护,怕受伤害。他承认自己有时会想太多。不过那种孤僻感也成了他营造人物状态的方式。“远离一个群体的时候我特舒服,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途径来说服自己。然后就造成了什么,人家觉得这孩子有心理问题,找人来跟我聊天。”
还是那个剧组,有场戏在夜市,围观的人很多,段奕宏溜边站在人群当中。休息时制片人“突发奇想”,摆了一排塑料躺椅搁着。“段儿,坐着,这就是你的椅子,坐吧。”
“啊,不用了不用了,真不用了。”他不愿躺着,拗不过,只好坐在椅子边上,“我不舒服啊。我不习惯你知道吗?包括我今天再想,那个时候我不到这个咖位,我坐不下去,我能理解这个孩子的心思。今天,老段到这个位置了吗?有人说你到了,你可以坐,好的。但我发现,我依然坐不下去,我在现场不会让自己懈怠成这个样子。久而久之,我变成了一个紧张体,并不是说我坐一个什么样的椅子就是不尊重了,它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。”
开门关门
接受采访时,“紧张段”倒没有那么拘谨。他很乐意听你的意见。说话时常常趴在桌上向上看着你,一额头重重的抬头纹和孩子气的表情,混搭起来却不冲突。
有一段说到剧情,他突然把手比成手枪开始演。送给他的杂志被他随手当作道具,不时翻起杂志的页角。有一句说到钱,他“哗”地把杂志推向前,“拿着。”有人会觉得这人“太爱演”,不如说他是聊得入港,进到了某种状态。
《烈日灼心》让他和邓超、郭涛在上海电影节上同获影帝。一路宣传,他不时地给邓超一个“公主抱”,甚至深情kiss。大学时最缺乏的弹性和“游戏状态”,今天对他似乎不再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。
“我还是变圆通了。”他笑笑。
真如此吗?
张建栋记得,段奕宏在“火”起来之前,曾经因为没有好戏和好角色,有过一段“沉沦”。“那时孙红雷还开导过他,别那么蔫儿吧唧、怀才不遇的。在影视界,你就需要去征服观众。为这个段奕宏还专门来找我聊天,但多数时候他不是那种很愿意和导演谈戏的演员。”
“这没什么不好。”一样不循常规的兰晓龙很能理解。“那些一天到晚跑来和导演聊戏的,好多我觉得并不一定靠谱。因为演戏这个事儿,不是能谈出来的。对角色的理解,是要靠内化的。老段他就是个关起门来想事、打开门来做事的家伙。”
拙于表达和沟通,偶尔顿悟,又想迈出和师长同道交流的一步,让段奕宏有种“顿顿挫挫”:“有时想透了,更多时候没想透。不是说好像纠正了自己一种能避免犯错的方式,它以后好像就水到渠成了,再下一个好像更行云流水了,不是。这种顿挫感可能会让我不那么世故。”
他的友党并不多,但好像交上一个,就“掏心掏肺”、无需废话。高虎特别喜欢段奕宏在《白鹿原》里的黑娃,“太好了,老段你终于会演戏了,再也不是脸上堆满肌肉和青筋了!”他说《白鹿原》能看出段奕宏做的功课,“也是深挖,可是是用巧劲儿了。”结果等两人一起合作《大时代》,照样因为路子不合吵到要停工,吵完又接着往下演。
何东被段奕宏请去看《西风烈》,看完老何“拂袖而去”:“我直接跟他说,这不就是一‘奔跑吗兄弟’吗?他听了‘呵呵’的,不说话。”
在何东眼中,老段的脸相相比从前更加坚毅、丰富。“现在段奕宏就缺一个逻辑分明、性格更突出的角色。”高虎则从心里觉得,那种贯穿段奕宏全部意识的“狠劲儿”和“神经质”,是演员特别需要的。“就像强尼·德普和艾尔·帕西诺,他如果能够克服性格局限,会有无限的可能。”
这些“最佳损友”都在从个人角度,为这位老相识做着憧憬和“设计”,听来有些遥不可及。真正能马上变现的,兰晓龙倒是提供了一个--明年是《士兵突击》10周年,他还没跟老伙计们说,自己正在筹备这部剧的续集。“团队很重要,袁朗我肯定还是要段奕宏来演。不然我宁愿去掉这个角色。不过,一定会有新东西。十多年了,部队也有革新,袁朗也会是2016年的袁朗。”他肯定无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