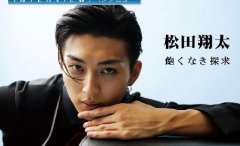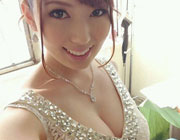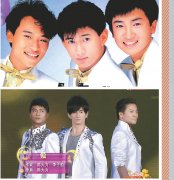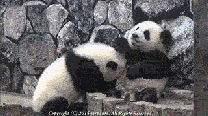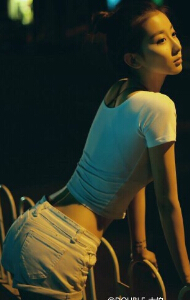段奕宏:戏里戏外完全不是一个人
已经成为“老段”的段奕宏说,年少时的自闭是一种自我保护,怕受伤害。他承认自己有时会想太多。
2001年的一天,导演张建栋在厦门一所监狱拍摄电视剧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。一个行将释放的“牢头”朝他走了过来。
“他忽然就阴阴地问了我一句,罗阳来了吗?”
“罗阳,没来。”张建栋心里打了个冷战。
那牢头“晃着膀子就走了”。张建栋这才恍过神来,自己3年前根据真实故事拍摄的警匪电视剧《刑警本色》,居然余波犹在。
角色罗阳的名字就是罪犯本名,曾被称为“内江第一杀手”,1994年在行动中被捕。“事隔那么久江湖上还有人惦记着他。一方面说明这是个人物,也说明剧里这个角色的完成度很高。”
出演罗阳的演员段奕宏时年26岁。彼时他的名字还叫“段龙”。
当时力排众议用段奕宏,张建栋看中的首先是他的眼神。“有股狠劲儿,凶煞寒冷,像冰一样。现在看,还能看到。剧中那个罗阳也不是普通马仔,是因为少年时受到欺侮凌辱后来转性,所以他眼神里不光是凶,还有一份纯真和执拗。”
那个剧组有王志文、李幼斌等好几位前辈,新人段龙并不发怵。“别人不敢接王志文的眼神,他敢。两人对视时,火星子乱溅。”更令张建栋惊讶的是,这个“愣头青”居然在谈酬金时毫不松口。“制片主任用那几个大牌压他,他不服,就说你们这样不公平,必须尊重我。”张建栋心一凛,“这孩子好有骨气。角色罗阳也是个底层啊,段龙我要定了。”
13年后,又是在厦门,段奕宏拍摄了他生平第一部大银幕悬疑片《烈日灼心》,演出个性复杂的警长伊谷春。其中大段和邓超扮演的协警、奸杀案疑犯辛小丰之间的对手戏,复杂微妙、纠结难言,同样通过眼神来完成。
部队出身的编剧兰晓龙形容段奕宏演戏既像水,又像容器。“比如张国强,他就是个容器。什么角色到他这儿,基本都是张国强。也挺好,味道对了,很有亲和力。段奕宏他既能包容,把角色装到自己里头,又能生出自己的内涵,这很难得。《士兵突击》里的袁朗就是段奕宏的袁朗,不是兰晓龙的袁朗。我觉得他这个版本更好。”
生活中的段奕宏却是老实而略为拘谨的。兰晓龙把老段比喻成警犬里的“黑背”:“每次演戏,总是一些‘诡变多端’的角色,最难演。但其实他这个人很守规则。包括他演死啦死啦(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主角龙文章)这样的,袁朗更不要说了,完全没有惟我独尊,很为别人考虑……还有,黑背很聪明。”
深度访问过段奕宏三四次的媒体人何东笑说段奕宏没城府,“他会莫名其妙地透支友情,骗他太容易了。”但下一句,何东毫不犹豫地说,“老段就是只藏獒啊。”
“你看他平常很谦和,如果真有男性触怒了他,他那个情绪会瞬间从零度蹭到100度,中间没有过渡。就像《刑警本色》里最后一个镜头,他和王志文(演的警察)同时举起枪。他一定会这样。”
“但那是戏里。”我说。
“他本人也会,我相信。老段跟你握过手吗?”何东问我。
“握了,特别有力。”
“对了。贼有劲儿,不像有些人,握起来蔫儿吧唧的。我感觉他很像香港演员刘青云。刘青云(塑造角色)更有丰富性,老段的爆发力绝对更胜一筹。”何东特别笃定地作结。“你看刘青云眉头一皱,我就好奇,不知他下一步要干嘛。段奕宏那根弦要是挑动起来,更可怕。对手很容易接不住,掉下去。人和藏獒对戏,你不是瞎努力吗?”
不要钢铁侠
伊谷春是中国银幕上不多见的警察:高度警觉,身手不差,但他的表情和眼神,对于同事兼疑犯的情感和态度,充满了“游离感”和“不确定”。
这种不确定性,正是段奕宏塑造这个角色的内核。但去厦门嘉莲派出所体验生活的过程,并不顺利。
一开始,他专门跟了一位平素全副武装的“标杆警察”。
“标杆曾经光凭第六感就抓获了人家后备箱里的毒品和枪支。那天我上了他的车,他看了旁边那车的哥们儿一眼,那哥们儿是光头,戴着大金链子,一看车牌,是一个外埠车。过去‘啪’一下就给记住了,然后跟我来了一句:你别靠近我。我说,啊?他说你别跟着我,给我站在10米之外。我还真想过,他要是发生了(意外),我是不是得报警啊。”
“标杆”过去给光头敬了个礼,检查了身份证和驾驶证,也打开了后备箱。段奕宏自觉光头看着不像“好人”,但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。
“没有,什么东西都没有。‘祝你一路平安。’驾车走了。然后这个警察回到车上,一脸遗憾。他没有抓到一个现行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,他还真不是在应付差事,还真盼望着有案件发生。‘宏哥,你今儿来了,我肯定会有好运。’我以为升官发财呢。什么好运?有大案要发生。”
这种在段奕宏看来有点“变态”的心理,让他在那一刻理解到了真实生活中警察的职业属性,和面临危难时压倒正常恐惧心理的“不正常处理”。
这段情境几乎原样复制到了电影中。“但是,他不是我想要的伊谷春。”段奕宏摇摇头。“我这次再去厦门,他当特警了,正如他愿了。(笑)可我不想要一个上来就像打了鸡血的警察,我不想他是一个钢铁侠。”
老段决定离开“标杆”,重新定一个目标。
最终成为影版伊谷春原型的家伙,是另一种“变态”。
“人家真的是歪打正着的8年刑警队长。一开始完全不屌我,好啊,太好了。”段奕宏的拧劲儿也上来了,“犯贱”一样跟在人背后,敬烟,套近乎--不奏效。
“这种人的警觉心和交流之间的这堵墙,是非常坚实的。”段奕宏干脆对他直言不讳,“不是带着目标和任务,我根本不可能接近你。你这样冷冷的外表啊,就挺变态的,谁愿意接触你?”
口子忽然就撕开了。两人从早上9点聊到半夜。
“都聊些啥?”
“我不能告诉你。因为他成了我一个朋友了。”段奕宏很认真地说。
后来,这位副所长情人节给老段发短信,说他“第一次和女友进了咖啡馆”。段奕宏拍戏时,有外地朋友来探班,全是副所长友情接待。影片去厦门点映,副所长出来送他。“我一看,眼泪汪汪的,都不忍心看,急匆匆上了车。发了个信息:我下面去喝茶,接你来,怎么样?好嘞。”
段奕宏说,所谓技术层面和职业共性的东西,以他今时今日的功力,捕捉起来不费力气。但他需要人与人之间接地气的情感,所以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:不确定性。“就是说不一味地凸显一个职业属性的特征。我要去找到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情感的交流系数。”